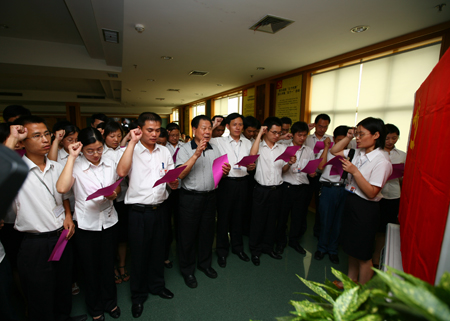[时政]
探访熟悉的陌生人
(新春走基层 新风扑面来)
 |
 |
北京站垃圾清运工郭长顺
以我脏苦换春运清新
本报记者李浩燃摄影报道
1月12日,春运进入第五天。早7点半,记者见到北京火车站垃圾清运工郭长顺,他已忙碌半小时了。
车站工作人员都热情地称呼郭长顺为“郭师傅”。郭师傅说,自己在北京站工作快四年了,这是经历的第四个春运。他1958年出生,大兴人,个子不高,佝偻着,额头和眼角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;身着保洁公司配发的蓝色上衣,沾满了各种污渍,穿黑裤子、布鞋;平头,仔细看去,已有不少白发。郭师傅住大兴区小红门附近,平时就倒985路公交车上下班,路上需要1个半小时,凌晨4点左右就得起床。早7点上班、晚7点下班——“一天净忙活了”。记者了解到,按规定保洁人员每周可以休息一天,但本来就缺人手,加上春运,基本是连轴转、无休。
郭师傅负责垃圾清运,“管辖”的区域以检票口一线为界,向外延伸至候车室、售票厅及东西办公楼等空间。车站时刻产生垃圾,他必须不停作业,将分布于各处的垃圾集中起来,再运送至车站西南门外的分拣场。他在第三候车室检票口一侧的过道里,放着用于中转运输的垃圾车,作为自己的“大本营”。平时,他就拖着一个垃圾桶随时随处收集垃圾,不断汇集到垃圾车上。
“让一下,嘿,让一下!”郭师傅拖着垃圾桶穿梭在不同的候车区域间,游刃有余。才半个上午,记者就跟丢了两次。他在工作中想出了许多提高效率的“土办法”,例如,每次尽可能多装垃圾,将大号垃圾桶拴上绳子,改装成可以手拉的垃圾车;把桶盖一侧竖起来,用收集来的木棍、废扫帚等插入垃圾桶四周,拿绳子捆起来加固,防止运输过程中垃圾散落,垃圾袋可以堆到两米多高;他对车次了如指掌,合理统筹室内不同区域的垃圾收集,利用检票后几分钟内客流较少的间隙,将垃圾清运到分拣场。郭师傅说,散的垃圾最不好弄,他要用手一点一点装进垃圾袋。每次转移垃圾他都小心翼翼,特别是一些藏着脏水的垃圾会滴漏在地面上,容易引起所在区域保洁人员的不满。因此,他每次转移垃圾车后,都尽可能清理下地面,有时还会用拖把拖一遍。
从第三候车室的垃圾“中转站”,到车站西南门的垃圾分拣场,无疑是一条充满物理障碍甚至人身危险的路。郭师傅身上随时揣着钥匙,用于穿行站台内外的各道门,随开随关,不能让无关人员进出;进入站台后,还要避让旅客;走到1站台尽头,仍须绕过一段狭窄的水泥路,这里不同类型的特种车辆往返穿行,必须时刻注意避让;出西南门后,路面不属于车站,土路泥泞难走,到垃圾分拣场还有个小上坡,此时不仅需要加大力气拖拽,还得注意路口的社会车辆。记者不禁在心里感慨,今天天气晴好,如遇雨雪天气,真不知郭师傅的这段单程近1000米的路要怎样走过。
临近1点,记者跟随郭师傅回到他的“大本营”。只见他蹲在垃圾车旁的角落略作休息,拿出自带的5个馒头、1包咸菜,就着候车室的免费白开水,凑合着就是一顿饭。
改装的“垃圾车”使用时间已久,加之常年“超载”,四个轮内的滚珠早已损坏,拉起来非常吃力。记者在站台上试着拉了一段,很难坚持下去。每次集满一车垃圾,大概耗时一到一个半小时,而顺利将垃圾车运送至分拣场并返回,得要半小时。如此往复,三趟下来,记者感到筋疲力尽,双脚仿佛已不属于自己,而这也只是搭把手而已。
在垃圾分拣场,记者跟他攀谈起来。老房子拆迁搬进楼房,老伴退休,儿子在公交公司当售票员,已经成家,为什么还要干这么又脏又累又苦的差事?郭师傅的回答很朴实:我靠自己每个月能挣2000元,能干一点是一点,“你不干,这么多垃圾,你说怎么办?”车站负责值班巡视的小张在一旁悄悄说,转运垃圾活脏又累,春运外地人过年都要回家,不好招人。
一车垃圾重则百斤,轻的也有五六十斤。该运第五车了,郭师傅看了看表说,今天垃圾不算太多,还差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了。“今年电话、网络订票的预售期比车站长,来北京站排队买票的人少多了。”
临别,记者向郭师傅伸出手,他迟疑了一下。那一刻,记者把他的手握得紧紧的……
北京站客运服务员孙更新
以我劳累换旅客舒适
本报记者程聚新摄影报道
1月12日,北京站发送客流量达到10.9万人。记者注意到,拄着双拐的小陈刚进候车大厅,就被头戴红色贝雷帽、身穿藏青色呢子大衣、脚蹬一双黑色皮鞋的孙更新给拦下了……
“需要什么帮助吗?”虽然嗓音难掩疲倦,孙更新的笑容可没一点儿折扣。这个大眼睛的23岁姑娘,是北京站的客运服务员。问过小陈的车次,默算了下开车时间,孙更新扭身分开人流,领着他往设在第二候车室的“素萍服务室”去了。
10多平方米的房间,三排长椅上几乎坐满了旅客:独自出行的老人,怀抱婴儿的妈妈,更多的是在京就医后返乡的病人。这些需要照顾的重点旅客,有的是孙更新巡视时发现的,有的由其他同事送过来。
今年春运,北京站实名制验证验票,暂停发售站台票。无人陪护的老弱病残孕乘客如何挤过春运的人潮、挤上火车,成为难题。孙更新所在的以铁道部劳动模范、北京站重点旅客服务室值班员李素萍命名的“素萍服务室”,成为北京站解决这一难题的抓手:既用作这些重点旅客的候车室,还得安排他们提前上车。
“1301次到满洲里的乘客请跟我进站上车了,需要轮椅送站的乘客请说一声儿”,孙更新安顿好小陈,便推着轮椅招呼起来。出候车室,上直梯,到二楼,转出相应进站口,或推轮椅,或跟担架,或帮旅客拎行李,孙更新一趟趟将他们送上站台,再找来列车长,请其照顾旅客。
孙更新告诉记者,平时,师傅李素萍和最小的师妹朝八晚五值日勤,她和其他5个女孩儿分成3个班次,轮班白夜倒,一工作就是12个小时,春运一到,加班也是常事。“白班加日勤也就4个人,夜班只有俩人,有时需要轮椅送站的重点乘客太多,我们就得亮绝活:一人推着俩轮椅上。”
记者发现,孙更新有几件东西不离身:两个本,一张纸片,对讲机,一大串钥匙。“这是重点旅客交接本,一式三份,服务室、列车、到达站分别留存,确保重点旅客全程列入特殊照顾名单;这是重点旅客登记本”,记者翻开重点登记本,娟秀的字体记录的是每位重点旅客的车次、到站、车厢座号、个人信息、陪同人数、病情,并写明所需的服务项目——几乎都是“送上车”。
为什么没记下开车时间方便乘客提前上车?孙更新笑起来:“跟师傅这么久了,哪趟车的发车时间记不下来?”但记者注意到,每到招呼旅客上车,孙更新都会掏出一张小纸片看一眼。
“这是‘四小时计划’”,孙更新将纸片递过来,背面用过,正面记录了最近的四个小时内,每班车的发车时间和上车站台,“发车时间好记,可站台每一天都不大一样,而且春运期间增开临客多,有了这个,就不怕耽误乘客上车了。”
正说着,孙更新举起对讲机应了一声,原来是同事发现重点乘客,即将送达服务室:要回牡丹江的陈先生夫妇,10岁的女儿刚动了手术,小姑娘不能走动,爸妈只好抱着她在候车人群里挤来挤去。离开车还有几分钟,孙更新找来轮椅,推起小姑娘,就领着一家人走了最近的通道,开门、开电梯。不大会儿,一行人就赶在进站人潮前上了车。跟列车长完成交接后,孙更新又掏出一张名片,是她的重点旅客服务卡:“下次有需要,就先打这个电话,我可以去接你们,省得孩子受罪。”陈先生接过名片,身边的妻子热泪盈眶。
夕阳时分,一直跟孙更新送站的记者,感觉脚脖子都快断了,可她却还活力十足。其实,这姑娘当然也累:巡视和送站需要走动10多个小时,几乎没休息;经常要面对几十位重点旅客,要记住车次、站台,出发前还要核对登车人数;回答旅客咨询时要五指并拢、面带微笑、上身微倾,或许只是指指方向,可每位旅客一句话,她可能要回答几百次;忙过了饭点是常事,甚至顾不得停下来喝口水。
可孙更新说:“这份工作更累的是心,身体反而顾不上。好在乘客的感谢和理解,哪怕只是一个眼神,都能够温暖自己很久。”
贵阳站铁路信号员王东亮
以我坚守换行车安全
本报记者龚金星智春丽
眼前两个大屏幕上跳动着红红绿绿的曲线,面前4个对讲机不间断地传来急促的指令……1月12日中午,当记者走进贵阳站信号楼操作室时,信号员王东亮正紧张地忙碌着。从早晨8点上班开始,她还没离开过座位。
“这里是车站的中枢神经,车到邻站后,我收到信号,安排股道,司机才能凭信号进站。一个车站只有一个信号员,平时90多趟车,春运加开到135趟,根本不能离开。”王东亮端起手边的茶杯,抿了一小口水,“不怎么敢喝水,连上厕所都是跑着去的。”
已经在车站工作15年的王东亮,以前是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。“老是坐着,又不动,还盯着电脑屏幕,近视300多度。”说到这里,王东亮显得有些郁闷。看得出来,她是个挺爱美的人,短发微微烫过,说起话来脆脆的。
墙角的充电器上,同时插了十几台对讲机在充电。操作室的一角放着冰箱、微波炉,王东亮和另外一名值班员的午饭通常都是就地解决。中午20分钟的空当便是午饭时间。
谈起春运期间的工作状态,王东亮直摇头,“这是我参加的第十四个春运了。一个比一个难,出行的人越来越多,车越开越多,职工还是那几个。贵州山地多,又会下冻雨,公路不安全,我们铁路的压力就更大了。”
“自从干了这个工作,我经常做噩梦,梦到信号发错了撞车。听说动车出了事后,我们单位每个人都要参加分析会,交一份自查自纠报告。”王东亮说,辛苦倒是其次的,信号员的工作最要命的就是压力大。
“我丈夫也在铁路上工作。女儿7岁了,家里好多年没有一起过过年了,我们经常是把年二十九当三十儿过。”说到家里人,王东亮脆脆的声音低了好多。“天气越恶劣的时候,我们就越要加班。下班后一听电话响,就提心吊胆……”
谈起新年心愿,王东亮低头想了一会儿,“很多人不理解铁路人,以为‘铁老大’就怎么怎么样,其实很多铁路人真的付出了好多。新的一年,希望大家对我们多些理解吧。”
记者准备离开操作室时,王东亮已经回到座位上又拿起对讲机了。
窗外传来一声汽笛长鸣,又有一趟列车进站……